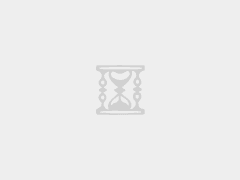许谦律师按语:
本文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利尔德·汉德法官1933年5月14日在哥伦比亚广播系统向全国发表的演讲稿。汉德法官(1872-1961)被认为是美国20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优秀法官之一,与卡多佐、布兰代斯、霍姆斯等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齐名。
这个论题与我们目前司法活动中的“法官心证、审判独立”等概念,有微妙的区别。
(美)利尔德·汉德 著
吕征 译
我之所以以“法官到底有多大自由裁量权”作为演讲主题,是因为许多人对这一主题心存困惑。在一些人看来,法官裁判案件应当遵循个人良心之引导,突破技术规则之束缚,因为这些技术规则与是非善恶毫不相干。在另一些人看来,法官裁判案件必须严守法律条文之规定,细研文本字面之含义,永远都是从“白纸黑字”中寻找答案。他们如此要求法官,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法官不应侵越政府权力,而行使自由裁量权就是越权。尽管这种理由无可挑剔,但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缺失。虽然我很担心这个主题有些抽象和乏味,但是它的确非常重要,至少可以让我们在很多方面取得某些共识。
我首先要阐释的问题是:何为法律。
究竟何为法律?法学家们已经争论了二千多年。一些人认为,法律应当包括当今社会中的习惯或者惯例,而一些人则主张法律仅仅限于那些由政府贯彻执行的规则。或许用语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在我论及的现代文明社会中,将法律一词之含义限于第二种理解对后面的分析更为方便。因此,法律并不是指普通大众通常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指他们认为正确的所作所为,当然也不是指那些精英们认为正确的所作所为。它仅指政府(不管这个政府是君主制还是议会制)强迫公民所遵守的,并以强制力为后盾的那些行为规则。如果确实如此,这些行为规则必然也会通过某种方式为人所知晓。法律就是政府的命令,并最终以某种确定的形式得以实施。
用以固化这些命令的唯一方式就是语言,而在现代社会就表现为书面形式。它们要么以正式的成文法出现,要么以国家授权的法官的判例汇编形式出现。法官先前的判例成为法律,这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理由,并且有许多国家不采用这种制度。不过在美国以及英联邦和英语语系的国家,似乎都是如此。或许本不该这样,但事实的确如此。无论在文明国度还是落后国家,总是由法官负责解释法律的真实含义,阐明政府发布其命令的真实意图。只有法官说话了,法律背后的强制力才得以体现。
解释法律看上去并不复杂,特别是当立法非常细致、详尽之时,似乎只要阅读一遍便可获得其真实含义。如果法律果真像科学原理、四则运算、音符高低那样精确的话,解释法律便简单无比。但实践往往并非如此,因为尽管政府颁布的命令都可成为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却不是随意而立。它必须得到社会普遍接受,符合日常习惯,符合公平正义,从而为人们广泛理解。此外,即使法律有其自己的语言,它也无力规范社会中的一切现象。没有任何人具有事先预测人类所有行为的能力,也不可能事先为各种行为确立完备的规则。比如,当两辆汽车相撞时,在全部案情尚不明了的情况下,我们就无从判断每个司机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法律也只是笼统地说他们应当“谨慎”驾驶,但是何为“谨慎”却未说明。结果,这个问题留给了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的成员来决定,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法律教育,其结论也就完全取决于陪审团成员的良知了。
正是因为法律不可能穷尽所有情形,而且法律语言与大众语言又无根本差异,这就有劳法官们从法律条文的文字中努力寻找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了。那么法官实际上是如何做的呢?尽管有时候法官自己并不承认,但事实上他总是按照这样的步骤去做:首先,他把法律规定或司法先例找出来放在案前;然后,他假设如果是由立法者或者做出先例判决的法官来处理这个案件,将会如何处理。法官们称这种方法叫做“寻找法律或法律原则的本意”。当然,法官并非总是这样,因为立法者、先前的法官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对新出现的情况作过任何评价,甚至目前所面临的情况从未在他们的头脑中闪现过。严格说来,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们曾经做出过什么评价,因为他们只是用书面形式做出了普遍适用于某一类案件的规定。如果坚持字面含义,要么会改变法律的本意,要么会做出相反的判断。因此对于法官来说,做出判决不能仅仅依靠字典。否则,他作出的判决可能会被每一个通达之人指责为脱离立法者的本意、违背法律的目的。
因此,法官在实践中一方面不能超越现行的法律和判例,另一方面又难以猜透立法者的预期。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尤其在法律规定模糊时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前面所说的两派观点,但是没有任何人会始终如一的坚持某一种主张,而往往是在不同情形下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采纳其中一种观点。在这两派观点中,一派认为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的字面意思,我称之为“字典”派。他们认为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法官必须逐字逐句、一丝不苟地适用法律。实际上,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法官做到自始至终严守本派观点,即便有人尝试过也不会坚持长久。试想,从来没有任何人会谴责医生在街头为抢救急重病人进行手术时引起出血现象,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不允许在街头发生流血事件。每个人都会认为,法律这么规定是为了阻止街头斗殴,而并不禁止上述情况。也就是说,虽然从字面上看,法律用语包括了上述情况,但是并不禁止为帮助病人而发生流血的情况。“字典”派一个最极端的荒谬例子是,一个罪犯因为起诉书的文字表达而逍遥法外。在该案中,由于法律规定的是“against the peace of the state”,而起诉书只是说“against the peace of state”,少了一个冠词“the”,于是该流派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解释法律,致使该罪犯成功地逃避惩罚。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法律中的每一个字都有具体含义的。
由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因此便有人主张法官不能过于追求文意,而应依赖良知和常识判断。但是,法官并不总能做得完美。如果给与他们过多的自由,则容易出现新的问题。尽管如此,另一流派坚决主张赋予法官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他们认为,法官不应该拘泥于严格遵循法律,因为这是在过去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幻想。法官应当按照诚信之人所认为正确的标准做出判断,而且他应当探究自己内心深处来寻找答案。我此前曾经说过,当人们解释任何书面文字时,或多或少–在美国,我们总是担心混淆各种权力,特别是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区分很难得到严格执行。不过,就像我们的宪法先驱们使我们坚信宪法一样,这种区分是一种良好的指南,但就像靠右行车一样,它不需要成为绝对的规则。我们的先驱们希望建立一个人民统治的政府,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立法权交给人民直接或者间接选出的议会行使。他们相信,这样的议会能够代表人民的共同意愿,不管他们认为的共同意愿是什么。这样的议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也不代表任何个人的意愿。他们只要知道任何个人认为正确的观点不能代表这种共同意愿就可以了,不论这里所说的“个人”是不是法官。他们或许曾经让法官充当这种共同意愿的代言人,由法官通过与大众的普遍接触实现这一目的。但是长此以往,法官就成了立法者,就像以色列的法官一样。不过,为了实现这种共同的意愿,他们又不得不给法官一定的空间,让法官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像立法者那样行为,否则法官不可能完成其承担的使命。所以,在制度设计上,我们便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把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混淆起来了。
不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谨记,他不能超越他所确信的立法意图。如果他心存疑问,便应当停下来,因为即便他确信自己知道公正的结果应该是什么,但他并不能确定社会各方冲突利益是否获得了平衡,他解释的共同愿望是不是真正的共同愿望。也就是说,即使法官的观点对争议双方更加公平,但他不能用自己的正义观代替立法者的观点,否则裁判的结果将难以反映大众的共同意愿,人民就不再是真正的统治者了。
由此可见,法官总是被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所牵制,从而处于两难困境:一方面,他不能贯彻执行他认为是最好的意愿,而必须把这个决定权留给代表公共意愿的政府(立法者);另一方面,他必须尽最大努力将这些意愿具体化,探求法律背后的真实含义,而不是毫无意义地附和法律的字面含义。没有人能够在这种困境中表现完美,伟大的法官只不过比我们做得好一些而已。事实上,为实现人类的自我主宰,法官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些困境。因此,当公众发现判决出现错误时,应当理解司法裁判的困难性。当人们批评法官“裁判不公”时,或许首先应当对法官所做的努力给予褒扬才算公平。当法官作出错误判决时,我们应当坚决将其收录于册以警世人,但批评者也应当深深理解司法功能所处的困境。
译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原载于《法律适用》2007年第2期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上海许谦律师 » 演讲:法官到底有多大自由裁量权
 上海许谦律师
上海许谦律师